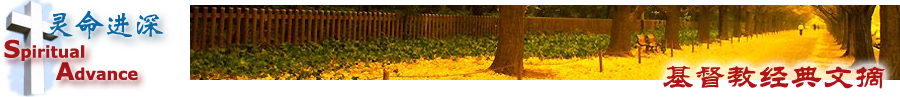
201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
201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1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1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2000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9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8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7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6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5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4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3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2年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1991年
九月刊 | 七月刊 | 五月刊
三月刊 | 一月刊
1990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9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8年
三月刊 | 一月刊 |
1987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1986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5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4年
十一月刊 | 九月刊 | 七月刊
五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3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八月刊
六月刊 | 三月刊 | 一月刊
1982年
十二月刊 | 十一月刊 | 十月刊
九月刊 | 八月刊 | 七月刊 | 六月刊五月刊 | 四月刊 | 三月刊 | 二月刊 | 一月刊
1981年
十二月刊 | 十月刊 | 七月刊 | 四月刊 | 一月刊
战区宣教硕果累累(五)
玛格丽.克赛特
七、婴幼儿
9月初,我们发救济前不久,有一个晚上,我丈夫、库克先生和一位传道士到镇西边的湖边散步,他们突然听到婴儿的哭声,仔细搜索之后,他们发现一个一个刚出生的女婴躺在湖边的山洞里,身下垫着破草垫,他们赶紧跑回家告诉我他们的所见。
“我们能把她抱回来吗?”约翰问。
我说:“你听我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女婴抱回来,马上就会有一屋子的女婴,今天一个,明天就是几百个。你知道吗,当地有个习俗一家不能有两个女孩子,如果生了女孩,他们就会这样处理,每天我们都听说有孩子被遗弃,这使我心碎,但是我们没有开孤儿院的能力,要是我们在这儿办个孤儿院,我们就地用毕生精力经营它。另外,你想想看,街上有多少流浪的孩子,年龄从蹒跚学步到十几岁,有的是父母双亡,有的则遭父母遗弃,就在今天我还听说,一个六岁的孩子满街跑,他的身边没有大人。我们坚决不能收留这个孩子。”
约翰哀求我:“可这个孩子是我们发现的,镇上的人说她已经被扔在那儿三天了,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她就会死掉的。”
“这也许很残酷,”我说:“没准儿死亡是她最好的归宿。如果我们把她抱回来,肯定不能收养她,还得找人抚养,我们对她的身世一点也不瞭解,说不定她是个长相丑陋弱智,到时候再送人,都没人要了,那将是个大麻烦。”
见我有些让步,约翰说:“如果你愿意抚养她,我承担责任。”
天黑后,他们把孩子抱回来,我解开髒兮兮的裹布,发现这是个未做任何处理的女婴,就连脐带都没剪断,她身上爬满了蛆,甚至眼睛耳朵嘴里都是蛆,看上去她只有一点气儿了,我挪动她时,她发出微弱的哭声,因为她太虚弱,我们不敢长时间挪动她,所以花了好几天功夫才把她洗乾淨。喂她进食更是困难,一开始我喂她稀释的羊奶,但她全都吐出来,后来我用凉开水喂她,她能咽下去,于是在凉开水里加几滴羊奶,每十五分钟喂她喝一小勺,然后我一点点加大羊奶的剂量,一连三周我昼夜看护她,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又不能停止教会的工作。11月1日,我终于熬不住病倒了,就在那天土匪佔领了霍邱镇——后面我还要讲这件事。
我们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富美,(寓意美丽幸福)但实际上她既不漂亮,过得也不幸福。她长成了一个身材肥胖的女孩,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智力明显不足,眼中总是透着一种傻气。在那个人人都逃难的日子里,想给她寻个人家实在不易。我们回国前就一直收养她,当我们要回国时,我们的佣人收养了她,他们承诺要好好待她,我们给她留下充足的钱财可以供她长大。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被骗了,那佣人家里有一个和富美同龄的女孩,他对富美一点都不好,我们离开不久,富美就死了。
****************
“我们能在你们的教会住下来吗?”一个难民说:“我老婆就要生孩子了,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镇上没人愿意收留我们。”
“可以让你们住一俩个晚上,但不能常住。”我说。镇上的人很迷信,他们认为孕妇把孩子生在谁家谁家就遭殃。他们会给孕妇搭个棚子,待生完孩子才能回家住。我求镇上的人收留他们一家,但大家都很固执没人肯收留他们。最终还是我为他们租了间房,看着他们安顿下来,得知他们的锅在路上被土匪抢走,我又把我家的锅借给他们用。这家人姓严,虽然穷,但还比较勤快,特别是三个孩子充满朝气。严先生和严太太经常来参加教会的学习,我给他们讲主耶稣是怎样被钉十字架替世人赎罪的,他们告诉我以前他们也结识过几个传教士,但从没有听过救赎的故事。
就在严女士要临产的前几天,她来找我说:“感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是逃难的,买不起贵重的礼物,我想把即将出生的孩子作为礼物送给你们。”
我非常吃惊,连忙说:“我可不敢要你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就够我忙的,还有这个捡回来的孩子,我有教会一大堆的事要做,真的没有精力帮你带孩子。”
她执拗的说:“我的孩子在你这儿会得到上帝的保佑,会得到良好的教育,我相信你会真心待他。”
我努力跟她讲道理,告诉她抚养孩子是她的职责和义务,我还跟她说也许她会再生个男孩,这样她就有四个儿子了,“四”字在中文意思中是大喜。她说她不想再要儿子了,养眼下的三个已经相当困难。
我又说也许是个女孩,将是个宝贝。她说:“不管生男生女,我都不要,我就送你了。”我斩钉截铁地拒绝收留即将出生的孩子,同时我又让她保证不对孩子下毒手。她无奈的回家了。几天后,他家大儿子前来送信,他家又添了一个小弟弟,我拿出几块布料,还给了他一些钱,“向你父母道喜啊!这几块布料给你弟弟做几件衣服,用这些钱买点必须品。”男孩向我鞠个躬,走了。
第二天,一个妇女抱着一个新生儿来了,她说:“我把孩子给你抱来了!”
“我的孩子!”我惊叫起来。
“是啊,”她说:“严女士今天一大早就走了,她让我把孩子送过来。
“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她昨天才生了孩子,今天就走了,她简直说话不算数。”
“她把孩子放这儿,没人知道她在这儿还生过孩子,他们现在已经踏上回乡之路了。”
“那他们把我借给他们的锅留下了吗?”我问。
“没留下,路上他们还得做饭呢。”那女人说着把孩子递给我,“给你孩子,你看他挺漂亮的,我喜欢他明亮的大眼睛和结实的小身板。”但我转身走了,我说:“我不会要这个孩子的,你收的,你养。”我这么说是依据中国的传统,但我内心也责怪自己,责怪自己太残酷。那女人绝望的哀求:“我家这么穷,养不了这孩子,我可怎么办呀?”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个老人一直站在我们身边,他是红十字会的,住在我家隔壁,听到那妇人的话,他二话没说,带着一个身着丝绸衣服的年轻人过来,那年轻人看了一下孩子说:“把孩子交给我吧,我收留他。”
妇人很感激,把孩子递给他,然后回家了。年轻人满脸笑容,抱着孩子进到隔壁的院子。我知道这小孩是找到了个好人家,会被当成宝贝。后来,我也没有追问那年轻人的来历,说心里话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打听他的来历。
一年半后,我们度假返回霍邱,当我们在蚌埠火车站下车时碰到了严女士,她看到我们抱着孩子就说:“天啊,这是宝珍吗?”
“不,不是,”我说:“这是佩珍,宝珍的妹妹。”我指着拉着我裙角的孩子说:“这才是宝珍。”
“她长大了,是吧?”严女士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出她满脸的焦虑,“快告诉我,我的孩子现在活得怎么样了?”我告诉她:一个有钱人收养了她的儿子。她接着就问:“那人姓什么,叫什么?”
我回答说:“我没问。”严女士长叹一口气,伤心地走了。
八、土匪
1938年10月1日的下午,我和约翰库克还有温斯特到城外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一连三天城门紧闭,城里一片备战的景象,护城的士兵挖战壕,筑机关枪掩体工事,城门口有重兵把守,城里是战斗前的紧张状态,死一般的寂静。我回到家,喂过孩子,哄他们睡觉,约翰和温斯特再次出去打探消息。
我边哄孩子睡觉边唱起摇篮曲:
主耶稣你可听到我,
今晚请你保护你羔羊的我,
你能穿越黑暗走近我,
平安光明你赐予我。
突然,我听到了枪声,我意识到战斗开始了,约翰和温斯特匆匆跑进家门,嘴里不停地喊着:“战斗打响了!”有一会儿,满城都是枪声和机关枪的嘟嘟声。
吃完饭的时候我对他俩人说:“听见了吗?子弹都打在院牆上了。”
约翰说:“感谢主,我们躲在屋子里。我出去看看吧。”
我说:“你最好别去,非常危险。”他还是走出屋,但刚走到院里就退回来了,“哎呀,太危险了,一颗子弹就从我耳边飞过。”
“今晚我们睡在客厅的地上吧,卧室的牆太薄,客厅的稍厚点。”听到我的提议,温森特把熟睡的两个孩子连同婴儿床一起搬到客厅,然后我们把席梦思床垫放在地上,我们静静地躺着听着外面的动静,子弹不断地飞过屋顶,掠过树梢,穿透树叶,打到牆上。城内的机关枪声响个不停,我感到肚子一阵剧痛,我流产了,当时没办法请医生,我只能忍着巨大的痛苦,我知道主耶稣就在我身边,温森特和我不停的祷告,求大能的主救助我。
到了半夜,枪声停了。几分钟内没有一点响动。突然传来妇女们的尖叫声。温斯特对我说:“一定是土匪进城了!”
我们再听,哪尖叫声越来越近,有人在攻隔壁的院门,这时从隔壁又传来女人们的尖叫声。温森特和约翰早些时候已经用麻袋把我家的院门牢牢堵住,以防土匪的攻击。后来我家家丁说那天夜里曾有三拨土匪欲入我家,但有人喊:“那是教堂。”
土匪说:“我们不洗劫教堂。”于是离开了。
我们躺在床上,依然不敢入睡,这时我们听到“咚”的声响,然后有爬牆声,之后又是“咚”的声响,紧跟着又一个,我问温森特:“是不是土匪进来了?”
他说:“我去看看。”他出门查看,我听到他和来人低声的说话,一会儿他进门告诉我:“是住我家边上的男人们,他们都翻牆进到我家院子,他们觉得我家是安全的地方,但他们把家里的女眷都扔在家里,留给土匪。”
“住我家两边的男丁都来了?”我问。
“是的。”温森特继续说:“他们都蜷缩在院角,浑身发抖。”
第二天早晨,温森特和约翰搬开挡门的麻袋,打开院门一看,土匪已经把街对面的衙门作为了他们的总部。不一会儿,一个匪首和卫兵来到我家,他进门时脚下的皮靴发出铛铛的响声,匪首挥动军刀向我施以军礼说:“牧师,你们什么时候召开布道会?”
温森特说:“每个晚上每个星期日早晨。”
“好,我们会来听。”他又行了个军礼,踏出院门。
一整天都有基督徒来告诉我这些土匪的暴行,陈传珍说:“我爸爸现在身体糟透了,因为土匪把他捆在房柱上,用点燃的香烧他的腋窝、脚心,让他交出家里的钱财,他现在严重烧伤,生命攸关。”其他来的人也讲了相同的遭遇,有的人已经因烧伤丧命。每个晚上和星期日上午的布道会都有土匪来参加,他们看上去彬彬有礼,我们简直不敢相信那些暴行竟是他们的所为。
一周后,土匪撤离了,街上又有人摆摊,卖旧衣服和各种物品,有些还是土匪撤离丢掉的东西。人们一旦发现有自家的东西,就立即买回去。
大约到了12月,土匪首领又回来了,这次他居然当上正规军的大官,他说他已经不再是土匪了,要过体面的生活,教会里的一个年轻人(于先生)作了他的警卫。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于先生穿着军服,挎着枪来到教会,我问他:“你给土匪头当警卫不是很危险吗?”
“不危险,”他说:“他已经不是土匪,而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了。”
我说:“我从没听过他前来忏悔,如果他没有从新作人的决心,即便他现在弃匪从戎,要改变他的土匪习性很难的。我非常担心你的安危,我劝你还是别给他当警卫了。”于先生似乎觉得我的担忧很多馀,一笑置之,继续他的警卫生涯。
1月,一队装备精良的队伍开到霍邱,这支队伍纪律严明,部队的将军走在队伍的前列。当我们看到这么一只精良部队时心想:“他们肯定要在这儿和日军决战。”日军依然驻扎在离我们十英里的地区。一天有人来报:那位将军逮住了原土匪头刘某某,同时将他相关的所有人关进监狱。
“那位于先生呢?”我们迫不及待地问。
“他也被捕了,”来人说:“很明显他是无辜的,会被释放吧。”
“有什么办法能救他出狱?”
“没有办法,不允许探监,他们不能和外人接触。”
“那会公审吗?”
“会有的吧。”来人答道。
三天后,我们站在院门口,看到所有的囚徒被押出来,他们都被捆着双手,脚上锁着脚镣,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押解士兵跟在后面,当我们见到其中的于先生时非常吃惊,我们曾听说于先生被释放了,我对温斯特说:“看,那是于先生。”
于先生像是听见了我的话,抬头看过来说;“牧师,我们天堂再见!”第二天,这支神秘的部队也消失了,日军仍然原地不动。
九、教会组织的受洗仪式
到了1938年12月底,我们在霍邱举行了第一次受洗仪式,那天天降大雪,还夹杂着冰雹,很多人因天气原因不能亲自来感受这神圣的时刻。我们感谢主使我们完美地举办了第一次受洗仪式,我们也庆幸没有太多的人来,否则我们的仪式不会这么庄严肃静。
二十四位圣徒走进圣池,然后是庄严的仪式。之后我们成立了霍邱教会,选举了临时理事,还任命了执事,这些负责人将工作到教会完全能独立开展传教工作。
一个月期间,只有一名会员离开了教会,其他人都坚信主。撒但不会轻易放弃作祟,但圣灵使教会不断壮大。
起初,教会挑选合适的人主持受洗仪式,召开布道会,成立各自的传道小组,派志愿者到各地传福音。主大施恩德,使我们的教会不断壮大,信徒不断增加,我们对主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我们的教会本着自立的原则,但在事奉主的事宜中也总能筹到钱。
教会成立的三个月后,我们回国休假,我们在教会举行了告别晚宴,把这些新信徒交到主手上,我们知道,主一定会施恩关爱祂的信徒的。
黑滋尔多德女士主动接替了霍邱教会的工作,她是第一个来我们教会的年长的传教士。她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直到另一个传教士接替她的工作,来人是乔治斯蒂得夫妇,教会在他们的带领下,得到主的庇佑,茁长成长。
我的姐姐露丝埃里特女士一直在河南的黄川传道,后来日军轰炸并佔领了那里,三个月中,她不停地掩护妇女逃离日军的魔爪,日军撤离后,我丈夫温森特去黄川接回露丝,让她和我们一起回国,因为在黄川的经历使她患上了精神紧张症,她需要回国医治。
我们乘坐一条小船离开霍邱,船舱特别小,一坐起来就磕到脑袋,我们只能躺着。第一天,河涨水,风也很大,所以我们走了不到五英里。下午二点左右,我们到达一处港湾,岸上有几户人家,船夫决定在这儿过夜,这时,我们听到一阵阵怪声,我们爬出船舱,看见岸上一群人吹着牛角号,手握长樱枪,“红樱会”,我喊道:“也许我们遇到土匪了,他们可是这一带最厉害的土匪。”
温森特说:“我出去看看,跟他们谈谈。”不久,只见他也吹起牛角号,过一会儿他回来说:“没错,他们是红樱会的,他们还命令我吹牛角号,他们的态度不友善,八成我们今晚会有危险。”
入睡前我们做了特别的祷告,求主保佑我们,之后我们睡着了。午夜我们被惊醒,听到牛角号声由远而近,船夫小心翼翼地把船划到河中央,但我们依稀可以听到号声,我们不清楚,那些被魔鬼佔据心灵的人会不会在离我们也就二三十尺的岸上朝我们开枪。我们再次祷告,求主保佑,我们静静听着子弹落在船边的河水中,岸上有人大喊大叫夹杂着牛角号声,更密集的子弹飞过来,吓得我们浑身哆嗦,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人群不断的呐喊,子弹不停地飞,一会儿,出乎我们的意料,号声逐渐远去,但听到旁边船上发出呐喊声,我们再次感谢主保护了我们!
第二天早晨,我们问船夫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平静地告诉我们:“红樱会确实来抢劫了,我们旁边的船是打鸭船,备有武器,他们开枪还击,红樱会看到他们有武器就撤了。”(续)